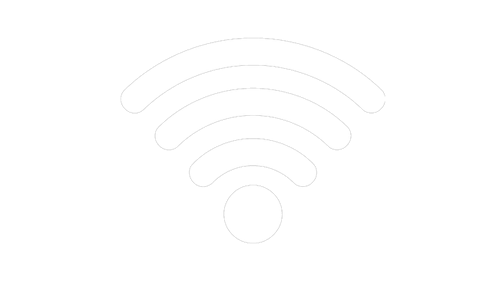历史棋局上的徐州:从龙潭逆转到六十万大军的绝地突围,为何最终仍难逃覆灭的宿命?
历史的棋局中,某些地理坐标似乎注定承载着深刻的兴衰隐喻。徐州,便是一个如此反复上演权力更迭与军事命运反转的舞台。它曾是国民党核心权力重构的关键节点,也曾见证抗战正面战场的首次辉煌,却又紧随其后陷入险境,更在数十年后预示了其大陆统治的终结。 昔日:从败走徐州到龙潭反击 回到1927年夏天,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继续北伐。然而,行至徐州,他却遭遇了孙传芳五省联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最终在这场交锋中败下阵来。这场挫败直接导致蒋介石于8月初宣布下野,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也随之转交到李宗仁、白崇...
历史的棋局中,某些地理坐标似乎注定承载着深刻的兴衰隐喻。徐州,便是一个如此反复上演权力更迭与军事命运反转的舞台。它曾是国民党核心权力重构的关键节点,也曾见证抗战正面战场的首次辉煌,却又紧随其后陷入险境,更在数十年后预示了其大陆统治的终结。
昔日:从败走徐州到龙潭反击
回到1927年夏天,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继续北伐。然而,行至徐州,他却遭遇了孙传芳五省联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最终在这场交锋中败下阵来。这场挫败直接导致蒋介石于8月初宣布下野,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也随之转交到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三人手中,由他们共同负责。
蒋介石下野后,孙传芳并未停止攻势,反而挟徐州大胜之余威,率军南下。他于8月26日倾巢而出,集结了11个师又5个旅,共计6万余人,趁大雾分两路偷渡长江,意图反攻南京。南京作为孙传芳昔日的“老巢”,在9个月前被北伐军攻占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此番有机会夺回,自然拼尽全力。

当时,南京周边仅有李宗仁、白崇禧的第7军和新成立的第19军驻守,何应钦的第1军则分散在南京到上海的沪宁铁路沿线,难以迅速集结。然而,李宗仁和白崇禧临危不乱,从容指挥部队。他们最终在南京城外的龙潭、栖霞山一带顶住了孙传芳的攻势,为第1军主力的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
随后,各部合力拼杀,经过连续六昼夜的殊死较量,北伐军终于大败孙传芳。孙部渡江南下的6万余人中,战死、淹死及被俘者接近5万人,仅万余残兵侥幸退回江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为此写下“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的对联,足见此役的重要性。
此役被认为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激烈、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经此一役,曾经显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变成了光杆司令。这场胜利也为蒋介石在1927年底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他迅速接管了孙传芳原本割据的江南富庶之地,并将其打造成了自己的基本盘。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麾下后来煊赫一时的嫡系中央军高级将领,如陈诚、顾祝同、刘峙、卫立煌、胡宗南、陈继承、熊式辉、桂永清等人,当时都以师、团长的身份参加了此役。作为主角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复出后丧失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把控,但都将龙潭之役视为自己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幕。特别是担任前敌总指挥的白崇禧,更是将此战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国民党另一元老谭延闿曾特意赠联“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给他,足见此役对其个人声望的提升。
意外之喜:台儿庄的狂热与徐州巨变
历史的车轮滚到193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中国第五战区指挥官李宗仁率领战区内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进犯徐州地区的日军第五、第十师团展开了激战。第五战区虽然当时被称为“杂牌军集中营”,但在李宗仁的人格魅力以及台儿庄官兵的齐心协力下,最终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此役中,号称精锐的日军两大师团,却因犯了“骄兵之计”,导致彼此配合极不默契,陷入处处挨打的局面。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一度让中国抗日军民士气大涨,毕竟这是国军第一次在正面战场击溃敌人。然而,在胜利的同时,一个巨大的危机又迅速萦绕在了徐州上空。
台儿庄的胜利极度增长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却也容易让胜利冲昏头脑。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一下子失去了理智。他发现了李宗仁军事指挥的厉害之处,认为既然如此,那就给徐州附近增兵,让他多打几次胜仗,最好能够将徐州地区的日军主力一口吃掉。他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兴奋,一下子将自己所属的中央军陆续从其他地方集结。
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徐州地区由原来的29万人一下子增加到了60万人,其中一多半是蒋介石的精锐中央军。战役一开始,李宗仁其实也同意蒋介石的方案,继续在徐州地区扩大战争规模,争取能够多吃掉几支日军,从而扩大胜利。他将整个战区分为鲁南兵团、鲁西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战术上依然采取主力投入一线、正面吸引牵制、侧翼攻坚的策略,从战略上看,基本上还是台儿庄地区的老战术。
而在日本这边,台儿庄的大败传到日军大本营时,也引起了内部剧烈的争吵,甚至一度按下了暂停键。日军内部此时也因为在中国问题上的战争而陷入争执不休,在东京出现了“扩大”和“不扩大”战局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如果继续陷入交缠,日军的战争资源必定继续朝关内倾斜,这将导致日本没有精力去防备苏联。而“扩大派”则认为如果不继续维持战争,以当时占领的土地无法维持自给自足和以战养战。
就在两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军队大规模往徐州方向集结的情报,让两方放下了争执。于是在台儿庄战役后不久,徐州又重新陷入战火之中。1938年4月10号,日军大本营下达了作战命令:华北方面军5个师团南下,其中第114师团进攻徐州,第五师团在徐州以东迂回截断中国军队退路,第10师团截断国军西进路线,第16师团配合第10师团,第14师团沿着陇海铁路夺取兰封,阻断河南方面的援军。
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派遣四个师团北上,与华北方面军南北夹击包抄徐州,企图将60万国军直接歼灭在徐州附近。由此,徐州会战也进入了第二阶段。

悬崖边上:李宗仁的清醒与绝地求生
1938年4月16日,日军第10师团猛攻临沂。由于此前驻守临沂的庞炳勋以及张自忠所部西北军并未从大战之中恢复元气,最终导致临沂失守,鲁南地区的一个战略节点丢失。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幸好滇军60军及时赶到,堵住了缺口,并和日军在禹王山鏖战。
这支滇军部队原本是为了参加南京会战而奉命出滇的,但还没到南京,南京就已经被日寇攻陷。之后,他们又奉命赶往武汉参加武汉会战,到达武汉后又奉命前往徐州接替汤恩伯的部队。然而,汤恩伯由于抵挡不住日寇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和滇军60军交接就先行撤退了。
此时,5万多日军已经大举直扑徐州,但李宗仁尚未完成部队调度。随着滇军的到来,暂时缓解了这一燃眉之急。在这之后长达27天,滇军60军像颗钉子一样死死钉在了阵地上,无论日军发动多么猛烈的攻势,始终无法攻破禹王山阵地。而这就为李宗仁之后的部署争取了时间。
同时,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也并不顺利。他们在这里遭到了桂军46军以及中央军52军两支部队的猛烈夹击。本身,他们在前不久的台儿庄会战之中就已损兵折将,尚未恢复元气,如今又陷入包抄之中。统帅部看到日军的两支军队在北线陷入焦灼,无疑认为又可以复刻台儿庄的胜利,于是继续加大了对台儿庄地区的兵力投入。
然而,随着部队集结越来越多,也让李宗仁开始清醒了过来。他不再像战役之初那么乐观了。此时,中国军队虽然挡住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南下攻占徐州的战略意图,可是华中方面的日寇却对徐州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原本华中方面军只有一个师团,而日军此时却派出了四个师团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问题在于,此时李宗仁手上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应付华中方面的日军了。

更可怕的是,徐州地区是一片平原,非常有利于机械化集团的作战,而这无疑就是日军的强项。如果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包围徐州,那么徐州这60万大军很可能重蹈淞沪和南京两次大战的覆辙。意识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李宗仁立刻将自己的担忧汇报给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此时还沉浸在台儿庄大捷的喜悦之中,并未听进李宗仁的建议。
李宗仁无奈,只得继续指挥部队进行战斗。不过好在李宗仁也留了一手,他提前准备好了陇海路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各部队突围的计划。正是这一手,最终拯救了60万大军。5月9日,日军攻克了蒙城,日军的包围网即将形成。5月14日,日军占领了陇海铁路,这意味着60万国军撤退的大动脉被日军掐断了。
到了这一步,就算是傻子也能够看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了。他们也看清楚了日军想要围歼60万国军于徐州地区的目的。在这地方如果继续和日军鏖战,等同于玩火自焚。这一次,蒋介石没有犹豫,直接命令李宗仁撤退。5月15日,蒋介石命令李宗仁率部撤退。可以说,蒋介石的头脑发热害苦了李宗仁,60万大军悄无声息地撤退谈何容易?而日军也准备一雪之前台儿庄大战之仇。
60万人的大挪移
奈何,日寇太小看李宗仁了。虽然蒋介石的胡乱增兵给整个撤退计划增添了不少麻烦,可好在李宗仁已经有了预案。他将60万大军分成5路,分别从各个方向突围:
一、李宗仁的长官司令部以及廖磊所部从安徽北部撤退,经宿县之后再折向西南突破日军的涡河封锁线。

二、汤恩伯军团以及机械化军团从河南东部撤退,突破宿县至永城的封锁线之后,再突破涡阳封锁线。
三、孙连仲以及张自忠所部西北军从安徽北部以及河南东部撤退,由台儿庄西南撤离,在突破永城的封锁线。
四、关麟征所部越过陇海铁路,从西北方向突围。
五、孙震部以及川军各部从徐州东南方向突围,在固镇与蚌埠之间过津浦线,由怀远西突围。
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原本固守禹王山的滇军60军必须继续死守,为主力部队突围争取时间。同时,为了拖延时间不让南北两路日军尽早会合,李宗仁还特地安排了特别能打防御战的孙连仲负责死守萧县地区。为了能够让整个突围行动顺利完成,李宗仁及其司令部等到所有的突围部队都撤退完了,才从徐州突围。
5月16日,徐州各部开始按照李宗仁的计划有序突围。考虑到大规模突围的目标太大,各部按照李宗仁战前的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将部队分散成团、营等作战单位撤离。至5月18日晚,此时徐州各部大部分已经从日军的缝隙之中突出重围,留下断后的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李宗仁命令滇军以及各部开始按照战前预定的计划突围。

日军没想到的是,他们精心准备的一张包围60万国军的大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李宗仁打破了。1938年5月底,当30万日军浩浩荡荡地在徐州会师之时,一下子傻了眼。他们在台儿庄以及徐州附近付出了几万鬼子的性命,最终得到的居然是一座空城。徐州突围战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次“败仗”,因为国军最终没有守住徐州。但是,它的意义却不能小觑。中国军队在此战中真正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同时为之后的武汉会战保住了几十万有生力量。这次突围是李宗仁自台儿庄之后指挥的又一高光时刻。
结语
时间来到了22年后,往日的一幕在长江南岸的同一地点似乎重新上演,却结局迥异。国民党军主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遭遇惨败,总计7个兵团另2个绥靖区,共80万大军覆灭。蒋介石最后的本钱消耗殆尽,不得不重施故技,第三次通电“引退”,宣布下野。政权再次落到了李宗仁、何应钦手中,此时李已经是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统,何则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白崇禧虽然不在南京,却手握20余万大军坐镇武汉,割据华中五省。

可以说,此时在长江南岸防守的军政领导班子,基本上仍是龙潭战役的原班人马。但此时无论坐镇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还是坐镇武汉、与南京遥相呼应的白崇禧,对复刻当年的龙潭大捷都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一方面,长江北岸的不再是日薄西山的北洋军阀部队,而是连战连捷、士气正旺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而统兵的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军神”级人物,不是孙传芳之流可比。
另一方面,自己一方的军权,掌握在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手中。他是南京高层里唯一没有参加过龙潭之役的。汤恩伯从抗战后期开始,就没有什么表现。1944年豫湘桂战役,面对江河日下的日寇,他手握30万大军,以逸待劳,最终却一溃千里,1个月内连丢38城,部队损失过半,其中不少是因纪律败坏被沿途百姓包围缴械的。解放战争期间,他更是每战皆负。国民党军头号王牌、号称“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就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全军覆灭于孟良崮战场。
不过,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忠心可嘉,因此蒋介石临走前授予其长江下游防守重任,总揽军事指挥权。李宗仁、何应钦空有其名,却对汤恩伯无可奈何。指挥官拉胯也就算了,关键是长江沿线的守军也都是乌合之众,大半都是从长江北岸甚至东北战场溃退回来的残兵败将,许多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被歼灭过,又临时拼凑组建,其士气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1949年4月,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彻底破裂。20日晚,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长江防线。22日,汤恩伯不得不下令总退却,妄图保存实力。23日,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李宗仁、何应钦逃往广州组建临时政府,汤恩伯则收拢残部逃往上海,企图继续负隅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