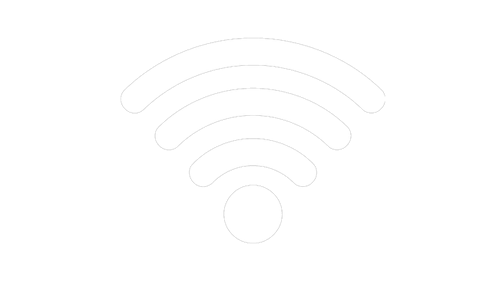归队直到鲁长山为救汤德远牺牲,才知,小贵为何死也要杀川野
谁能想到,地主家的小少爷田小贵,最后会拖着残废的身子扑向川野的枪口? 当731部队的魔药在他血管里烧灼时,是那个总喊他儿子的老排长鲁长山的死,把他从地狱里拽了出来。 田小贵的人生本不该这样。 他本可以躺在金银窝里当少爷,却偏要钻林子里打鬼子。 队伍被打散那几年,他逃回家却被日伪追杀,连累得家里鸡飞狗跳。 好不容易躲过追兵,又被汉奸抓进黑牢,那双能百步穿杨的手,被烙铁烫得连碗都端不住。 更惨的还在后头。 日本人把他扔进731部队当药人,代号490的药剂打进身体后,他经常像条野狗似的发狂。 最要命...
谁能想到,地主家的小少爷田小贵,最后会拖着残废的身子扑向川野的枪口? 当731部队的魔药在他血管里烧灼时,是那个总喊他"儿子"的老排长鲁长山的死,把他从地狱里拽了出来。

田小贵的人生本不该这样。 他本可以躺在金银窝里当少爷,却偏要钻林子里打鬼子。 队伍被打散那几年,他逃回家却被日伪追杀,连累得家里鸡飞狗跳。 好不容易躲过追兵,又被汉奸抓进黑牢,那双能百步穿杨的手,被烙铁烫得连碗都端不住。

更惨的还在后头。 日本人把他扔进731部队当"药人",代号490的药剂打进身体后,他经常像条野狗似的发狂。 最要命的是鬼子逼他当暗桩——把救命恩人鲁长山的位置卖给日本人。
那年冬天在宝局门口,药劲儿又上来了。 他看着鲁长山跟汤德远从胡同口走来,喉咙里像卡了把刀。就在汉奸赵庆田从对面茶馆掀帘子的刹那,小贵突然扯着嗓子吼了声:"卖炭的往南走啊! "老山东的烟袋锅子立刻掉在地上,拽着汤德远翻进后巷。 枪声在胡同里炸开时,小贵瘫在墙角抠烂了自己的膝盖。

鲁长山到死都不知道那天的暗哨是谁。 这个山东大汉把最后一把子弹压进枪膛,冲着被川野包围的汤德远他们喊:"二班长带人走! "转身就往反方向的桦树林跑。 追击的机枪响了大半柱香时间,福庆找到他时,老山东胸口的棉袄都被血浸透了,手里还攥着包给田小贵留的烟叶子。
消息传到小贵耳朵里是三天后的清晨。 福庆蹲在磨盘旁,话没出口先抹了把脸。 田小贵整个人直挺挺地栽进雪堆里,冻土渣子糊了满嘴。 没人敢过去扶,谁都知道老山东给这孩子洗过头上的虱子,小贵犯药瘾咬伤自己的时候,是老头子让他咬着胳膊熬过去。 雪地里突然传来"咚"的闷响,小贵跪着磕了三个带血的响头。

汤德远接过了排长的铁哨。 他蹲在炕沿部署围捕汉奸肖铁林的计划时,田小贵突然捂肚子往外跑。 大伙以为他拉稀,哪知道他躲进马棚,掏出匕首就往大腿上扎。 刀刃刮过骨头的咯吱声里,血顺着草垛往下滴。 这样狠的疤他腿上有七八道,都是怕药瘾犯了说出战友行踪时拿命熬的记号。
真正让他豁出去的还是川野。 那个杀红眼的日军少佐剁了汤德远的独子,又设局逼鲁长山入套。 在肖家大院门口,田小贵看见川野的军刀在太阳底下发亮,突然想起老山东被送葬时盖的那张破草席。 残废的十指在绑腿上搓了又搓,他从柴堆里抽出杆老套筒——那枪托还是鲁长山替他削的。

当川野的吉普车经过城隍牌楼时,对面屋檐上滚下个黑影。 炸膛的老枪迸出火星的刹那,小贵整张脸都糊着火药渣,子弹却准准掀飞了川野的半片头盖骨。 宪兵队的子弹把他打成筛子前,这孩子咧着烧焦的嘴笑了下。 没人听见他最后嘟囔什么,只有庙前卖豆腐的胡婆看见,那孩子咽气时攥着块焦黑的烟叶子。
汤德远他们冲进肖府时,川野的死讯正在伪军里炸了锅。 肖铁林抱着满匣子金条要钻暗道,被福庆薅着后领拎出来。 这个祸害东北多年的汉奸头子,在枪管抵住太阳穴时终于吐露了秘密:大秃子岭的碉堡底下埋着三吨炸药。 后来反攻的部队冲上岗楼时,绕开炸点的路线图就写在汤德远的烟盒纸上,那是照着田小贵遗物里半张地图补全的。

八棵松的老槐树下又响起集合哨时,高云虎用袖子擦了擦三块新木牌:鲁长山、兰花儿、田小贵。 福庆把缴获的东洋烟卷点了三根插在碑前,青烟顺着风往林子里飘。 汤德远没说话,手指头死死捏住口袋里的烟叶子包,磨得发亮的铜哨齿痕深得像谁咬下的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