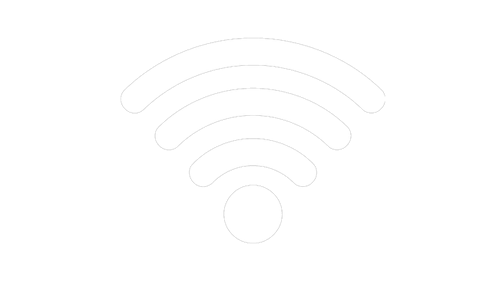哥伦布首航:从模糊航线到世界重塑,探析其航海技术与认知变革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首次跨大西洋之旅,不是偶然,也不是简单一蹴而就。他的航程开始前,内心已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这种坚定,源于他长期的航海积累,对洋流和风力系统的深刻理解,更包含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早期线人信息。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马丁·阿隆索·平松。他到底掌握了什么知识,能让哥伦布如此重视,甚至认为这些信息对整个探险至关重要?这成为开启这场史诗旅程的一个引人思考的谜团。 路线琢磨,步步为营 哥伦布自己曾深入爱尔兰北部海域,也曾在赤道附近航行。这些经验让他明白,那些区域不适合作为跨洋远征的返航路径...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首次跨大西洋之旅,不是偶然,也不是简单一蹴而就。他的航程开始前,内心已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这种坚定,源于他长期的航海积累,对洋流和风力系统的深刻理解,更包含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早期线人信息。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马丁·阿隆索·平松。他到底掌握了什么知识,能让哥伦布如此重视,甚至认为这些信息对整个探险至关重要?这成为开启这场史诗旅程的一个引人思考的谜团。
路线琢磨,步步为营
哥伦布自己曾深入爱尔兰北部海域,也曾在赤道附近航行。这些经验让他明白,那些区域不适合作为跨洋远征的返航路径。相反,巴斯克斯关于“特伊夫航行”的报告,给了他新的启发。

亚速尔群岛纬度的航线,确实适合返程,但对去程来说并不理想。如果被迫航向佛得角那样属于葡萄牙的专属海域,风险巨大。如此一来,只有借助信风力量的加那利群岛走廊,成了唯一可行的西向通道。
于是,航行计划敲定。那年8月3日,探险队正式启程,驶向加那利群岛。经过补给和准备,船队在9月6日上午从戈梅拉港出发,正式进入茫茫大西洋,一路向西。
尺规天地,双重标准
哥伦布在日志中记录了每日的航行距离。他定下了一个“每联盟四英里”的换算比例。这个信息很有意思,却也抛出了新问题:哥伦布所说的“英里”和“联盟”究竟是什么概念?他脑海里的度量标准,与当时的普遍认知有何不同?
后来从《华尔街日报》的记录里可知,哥伦布与远征队的其他飞行员分享了他的测量方法。大家认为,他所用的基本单位,大致相当于卡斯蒂利亚联盟。哥伦布日志中呈现的“英里”数值,更接近波托拉纳英里(约1250米),而非罗马英里(约1480米)或卡斯蒂利亚英里(约1393米)。
船队里实行了一种“双重计数”——海军上将哥伦布自己一套,三名舰艇驾驶员又各有一套计算方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避免水手们因为漫长航程而感到气馁,维护士气。但背后,或许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此外,葡萄牙的航海经验对哥伦布在大西洋早期航行阶段(1477年至1484年间)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度量上。在地中海,飞行员和包租船员习惯用每里格三英里的比例。但在大西洋,却反常地使用四比一的比例。
地图指引,拓新边界
哥伦布在航行前,广泛参考了当时的制图学知识。他曾接触过祖恩·皮齐加诺、安德里亚·比安科和弗拉·毛罗等人的地图。例如,皮齐加诺在1424年的副本中,除了已知群岛,还描绘了一些神话般的岛屿,其中两个面积相当大。
比安科绘制了几幅大西洋地图,并在1436年的作品中提出了“海洋岛屿”的设想。他还是弗拉·毛罗的合作者,并在阿方索五世统治时期被葡萄牙人咨询过。哥伦布很可能使用了比安科1459年的对应副本。
尽管没有明确记载,但克里斯托弗可能也研究过1489年至1490年威尼斯科尔纳罗地图集的一些地图。胡安二世的保密规定,使得获取葡萄牙语地图副本(如1471年的匿名副本或1485年的佩德罗·雷内尔的副本)更为困难。
托斯卡内利的著名地图,对哥伦布的计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该地图的原始样本未能流传至今,但人们根据其信件中的描述,重建了它的设想。这张地图涵盖了整个海洋空间,右侧是欧洲(最北端爱尔兰)和非洲(最南端几内亚)海岸,左侧则描绘着遥远的东方,大西洋上则分布着葡萄牙、卡斯蒂利亚群岛以及中世纪传说中的神话岛屿。

其中,位于西潘戈群岛和伊比利亚群岛之间的安提利亚岛和圣布兰丹岛的描绘,是这张地图的核心看点之一。整张地图的设计遵循网格系统,距离以“联赛”为单位标示。哥伦布很可能确实接触并研究了托斯卡内利的地图。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和制图师,他理所当然地会将托斯卡纳圣人的信息与其他图表资料结合起来,用于他著名的第一次航行。
磁偏角的迷思
哥伦布本人根据他的证词和拉斯卡萨斯的记录,确实携带并咨询了托斯卡内利的地图。尽管地图具体内容主要通过对托斯卡内利影响的推断得出,但远东地区的划分,无论是佛罗伦萨学派(国泰和芒吉的部分区域)还是马泰勒斯学派(南半岛的革新贡献),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大片海洋上,葡萄牙-卡斯蒂利亚群岛弧线与西潘戈框架在网格系统中的位置,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这张航海图的具体内容,我们知之甚少,只能根据地理评论或日志中记载的“失败”之处进行推断。
航行中,哥伦布遵循的路线与托斯卡内利信中建议的路线有所不同。基于他对西潘戈假定位置的判断,哥伦布决定选择更为偏南的方向。
在大部分航程中,海军上将的船队沿着戈梅拉岛的纬度平行航行,直到9月19日。当时不清楚他是否产生了疑虑,或是为了寻找某个参考岛屿。接下来的几天,航向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恰逢船队抵达马尾藻海。9月24日,船队恢复了西向航线,并一直保持到10月7日。随后,船队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主要航向西南偏西,只有一天是纯粹的西南方向。

哥伦布坚信他们正在岛屿之间航行,并采纳了马丁·阿隆索·平松的建议改变了航线。尽管如此,哥伦布仍表达了担忧:如果他们未能接触到西潘戈,可能就无法抵达遥远的东方海岸。
海军上将估算,他们已经轻松超越了安提利亚岛的长度。除非他们对航线进行大幅修正(转向西北或西南),否则他们应该遇到的下一片陆地便是西潘戈岛。
哥伦布和平松之间的导航标准是否仅仅不同,还是也反映在他们各自的制图理念中?当他们在9月25日就未发现岛屿一事交换意见时,那种惊讶源于一个奇特的现象。
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两次提及的这一长期航行中遇到的感知对象,正是当时令人费解的磁偏角现象。这种现象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是向东偏转的(指南针指向“东北”)。然而,当克里斯托弗开始他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时,磁偏角却偶然地转向了西方。
新世界旧框架
10月12日清晨,探险队首次在美洲大陆登陆,那是一个巴哈马群岛的小岛,海军上将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他当时认为这个岛与耶罗岛处于同一纬度。在描述了这个岛屿之后,哥伦布表示他渴望去探索西潘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参观了几个卢卡亚群岛的岛屿,对当地人民和岛屿的样貌感到惊奇。

这次发现并非立刻被完全理解,哥伦布面临着如何将所见之地融入其地图表示的难题。海军上将提议以“尊重”原则来绘制海图,提供方向和比例网络(后来他会尝试融入天文数值),并辅以托勒密式的书籍或地图集(标注纬度和经度)。
他在葡萄牙学习到,要将任何新发现纳入地理学范畴,必须使用地理坐标。即使只是一个有缺陷的纬度,也比仅仅依靠方向和距离来定位一个地方要好。
哥伦布沿用了葡萄牙航海员的测绘程序,但在西印度群岛面对全新的地理条件时,他懂得如何进行必要的修改。哥伦布在通过估计来确定纬度的方法中引入了一项重大创新,即在海图上测量从赤道到目标纬度点的子午线距离,这一数据从航程的“失败”中获得。
哥伦布并未在公海上直接确定纬度,他始终依赖估算程序航行。尽管他在《日报》中声称使用象限观察极星高度,但这主要是为了验证分配给船只的“失败”的准确性,将仪器更多地作为导航的辅助工具。
在群岛巡游期间,哥伦布了解到古巴的存在。他试图将这一地理现实与他对远东的想象相匹配,坚称自己已到达安的列斯群岛最大的岛屿,并且确信那已经是大陆的一部分。
因此,古巴必须对应于位于他所寻找目的地东部或东南部的岛屿之一。在古巴北海岸附近,靠近预定目的地的设想得到了加强,这促使他对西北沿海延伸区域进行考察。仅仅三周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新尝试中,他重复了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些数值都对应的是磁方向,没有经过校正。在考察伊斯帕尼奥拉岛北海岸时,海军上将还获悉了离大陆不远的南部(牙买加)有一个岛屿的情况。

航海新篇章
最终,在一月中旬,哥伦布决定启程返航。在犹豫是否要继续探访加勒比群岛和亚马逊群岛之后,他选择了直接返回,沿着大西洋寻找有利的风向,以期相对较快地抵达亚速尔群岛。
这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发现”。它更是一次深刻的认知革命。哥伦布的坚定信念,他所依据的旧有制图理论,以及航行中遇到的种种未知挑战,共同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他试图将新发现的世界强行纳入其对亚洲地理的既有框架,这种执拗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推动他不断探索的动力。
哥伦布的航程暴露了传统知识的不足,迫使航海家们重新审视并改进测量和制图技术。他的实践推动了从经验航海向更科学、更精确航海的转变。这不仅开启了全球探索的新时代,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对地球面貌的理解,标志着一场认知与地理学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