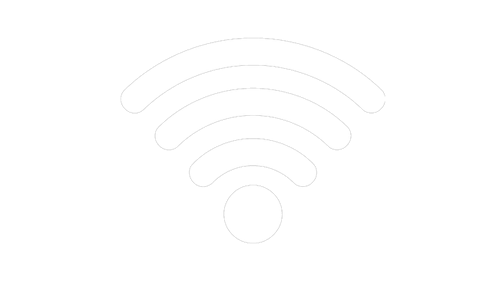铁拳出击:步兵11师如何重创印军第4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1师,源自原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3旅,系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的西北红军中仅存的两支完整体制部队之一。该师在全军师级单位中拥有最多的红军连队,历经艰苦卓绝的战斗,遍布我国最艰苦的地区,因而赢得了“踏遍新西兰”的崇高赞誉。 陕北红军传人 11师的历史渊源错综复杂,其前身汇聚了陕北、陕甘边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众多红军游击队,并融入了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部。经过多次整编与合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追溯至1932年3月,最早的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便是其前身之一,随后又发展出了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1师,源自原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3旅,系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的西北红军中仅存的两支完整体制部队之一。该师在全军师级单位中拥有最多的红军连队,历经艰苦卓绝的战斗,遍布我国最艰苦的地区,因而赢得了“踏遍新西兰”的崇高赞誉。
陕北红军传人
11师的历史渊源错综复杂,其前身汇聚了陕北、陕甘边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众多红军游击队,并融入了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部。经过多次整编与合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追溯至1932年3月,最早的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便是其前身之一,随后又发展出了红27军84师、陕甘宁军事部、陕北红29军、陕甘宁独立师、陕甘宁红2团、陕北独立第1师等组织。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陕甘宁军事部被改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至1942年底,该部又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旅部,由贺晋年担任旅长,王世泰担任政治委员,下辖警7、8、9团。1946年4月,红四方面军第4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385旅并入警3旅,黄罗斌任旅长,郭炳坤任政治委员,下辖警5、7、8团。1947年9月,警3旅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到了1949年2月,警3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11师,由郭炳坤担任师长,高维嵩担任政治委员,原辖各团依次更名为步兵第31、32、33团,全师共有5700余人。
31团源自于陕北红29军、陕甘宁独立师以及陕甘宁红2团的辉煌历史。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该部队进行了改编,先后成为八路军129师特务营、工兵营,后转隶留守兵团警2、7团。至1942年12月,该团正式编入385旅,成为警4、5团。1946年4月,警4、5团合并,组建为警3旅5团。作为一支红军团,该团以突击力强著称,始终是军师的主力战斗部队。
32团的前身可追溯至陕北的红27军。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该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的辎重营与炮兵营,后来又成为留守兵团警1团。到了1942年12月,警1团与边保司令部第4团合并,成立了警3旅的7团。至1946年4月,原警3旅的9团以及三边保安团的一部分亦被吸纳进警7团。作为一支红军团,该团擅长防守,战斗力出众,是军师的主力编制。
33团的前身系1937年1月成立的陕北红军独立第1师。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该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特务营,继而演变为留守兵团警5团。至1942年12月,警5团与边保司令部的富甘独立营合并,组建为警3旅8团。到了1946年4月,原警3旅9团及三边保安团的部分力量并入警8团。该团不仅是一支红军部队,更以强大的战斗力著称,擅长独立作战。

1949年2月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以及副司令员张宗逊,共同驻守在西北战线的最前沿。
11师部队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三个步兵团队均为红军编制,且全师拥有二十余个红军连队。在抗战岁月,该师的前身各部在留守兵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及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秉持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坚守在陕甘宁边区。他们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多次反共挑衅,圆满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以及陕甘宁边区的神圣使命。
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11师(警3旅)英勇无畏,先后投身迎王战役、延安保卫战、挺进关中、开辟黄龙新区、宜瓦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澄合战役、荔北战役、1949年春季战役、陕中战役、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以及兰州战役等数十场重大战役战斗,总计82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共歼灭国民党军36000余人,为解放大西北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该师的战斗足迹便未曾停歇,直至1967年10月。其作战历史之久远,战斗经验之丰硕,在人民解放军中实属罕见。在这数十年的战斗生涯中,该师孕育了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勇于牺牲、不畏疲劳、敢于攻坚、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与坚韧作风。部队始终秉持党的指引,不居功自傲,不讨价还价,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忠诚老实,任劳任怨,长期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原第四军军长、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张达志将军曾高度评价11师:“这支队伍作风朴实,不夸大其词,不空谈理论,不吹嘘,不虚浮。对他们下达的任务无需他人催促,执行得扎实、出色。他们的工作经得起检验、考验,这是大家的共识。”
奔袭耀县
1947年五月,为协助我西北主力部队围剿蟠龙之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代司令员王世泰,率领警1旅3团与警3旅5团,在邻近部队的支持下,对咸阳至榆林公路上的关键补给基地耀县,发动了一场跨越长距离的快速突袭。
耀县城池历史悠久,其城墙巍峨耸立,高达约10米。城内驻守着陕西保安7团、整85旅辎重营、特务连、耀县专署、县政府以及警察和野战医院等众多力量,总人数逾2000,形成了严密的火力防御体系。尽管城池易守难攻,然而敌方的守备却显得松懈,系统繁杂,单位众多,指挥体系未能统一,这正为我军逐个击破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团受命增强旅工兵连、山炮连的实力,于5月4日下午4时,从文王山、武王山一带出发,迅速向耀县发起突袭。为确保五团行动的顺利进行,警1旅的3团暂时归入警3旅的指挥之下,悄无声息地进驻耀县北部的泥沟子地区,构筑防御阵地,以阻挡从铜川方向赶来的援敌。同时,该团的三营被指定为警3旅的预备力量。此外,警3旅的骑兵侦察连等部队亦担负起阻击来自富平和药王山方向的援敌的任务。

警3旅的首任旅长为贺晋年,而首任政委则由王世泰担任。
5月5日凌晨3点钟,我5团抵达耀县北关,敌军尚未察觉。在主攻1营悄然攀登城墙时,发现北城墙既高又坚,原先携带的云梯长度不足。战士张思义随即向营部报告:“耀县城东北角的城墙较低,易于攀爬。”在团部批准后,1营立刻调整战术,转移至城东北角。至4点钟,1营的2、3连迅速搭建隐蔽的云梯,悄无声息地登上城墙,守敌依旧毫无察觉。
两个连队随后分别沿城墙向南、西两个方向展开行动,城上守敌在沉睡中成为了俘虏。至6点钟,四周的城墙已被我军完全控制。这时,耀县地区的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阎崇师听到枪声,误以为是城内的保安队与整85旅发生了冲突,便急忙带领两名卫兵向城北门走去,同时大声呼喊。我3连机智应对,诱使阎崇师及其三人登上城楼,成功将其生擒。
我军迅速把握战局主动,5团指挥工兵连成功炸开东城门,3营作为先锋,率先闯入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2营则向东关及火车站推进,扩大攻势;1营则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城墙四周,其余主力与3营并肩作战,投入巷战。3营的7连迅猛攻入敌保安7团团部,生擒敌副团长及其部下数人。9连也迅速占领了邮电局、银行等关键设施,当其推进至敌整85旅辎重营大门时,遭遇敌地堡群的猛烈火力阻挡。我突击队一部迅速攀爬房屋,另一部则沿街巷接近敌地堡群,然而由于敌火力过于猛烈,连续两次攻击均未能成功,遂暂停攻势,巩固既得阵地,并组织炮兵对敌地堡群和营房进行精确射击。
在炮兵部队的强大支援下,3营奋勇冲击,成功突破敌军阵地,重创敌军主力。战至午后一点,城内东南、东北以及西南的街巷之敌悉数被歼,剩余敌军退守至县政府、钟鼓楼以及城西北角,展开顽强抵抗。5团随即调整战术部署,指定8连作为突击部队,负责攻克钟鼓楼。在炮火的掩护下,8连的攀爬小组抵达架设点,却遭遇钟鼓楼前照壁后隐蔽堡的猛烈火力,造成较大伤亡,攻势受阻。5团于是将9连改为突击部队,并指令1营积极行动,牵制伪县政府和城西北角的敌军,同时命令山炮连迅速前进至东大街,占据有利阵地,对钟鼓楼进行近距离炮击。3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9连趁机发起猛攻,短短15分钟便攻克了钟鼓楼,歼敌百余人,其余敌军退至县政府院内,继续负隅顽抗。
与此同时,原计划攻克火车站的2营5连,由于局势突变,未能如期渡过河流。而6连则迅速转向东关,成功占领了野战医院,并全歼了敌军200余人。5团随即命令2营控制东关,以阻止火车站方向援敌的进攻,确保我军右侧的安全。到了下午5时,接到敌援兵即将抵达的消息,5团迅速组织部队依托城墙与钟鼓楼进行掩护,协助民工搬运物资和武器弹药。至晚上6时左右,县政府院内之敌连续发起反击,但都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我方友邻的3团也在顽强地阻击从铜川来的援敌。在我军完成物资搬运任务后,已成功达成了奇袭耀县的目标,于黄昏后主动撤离了战场。
在耀县战役中,我5团采取远距离突袭,出其不意,取得了显著胜利。在巷战阶段,我军迅速分割敌军,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动,灵活调整战略部署,集中兵力与火力,协同作战,接连攻克敌方阵地。此战共歼敌少将专员以下1020人,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步枪、手枪1500余支,以及其他大量弹药和物资,树立了光辉的战例。此次战斗,为我军首次攻克关中地区铁路线上的县城,令胡宗南集团震惊,一度切断敌后补给线。部队入城后,严格执行军纪,秋毫无犯,极大提升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力。战后,5团荣获上级通令嘉奖,荣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西府陇东战役之谜
1948年春季,从4月16日至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展开了为期27天的西府陇东战役。此战收复了延安,攻占了洛川,进一步扩大并加强了黄龙解放区的安全,共歼敌2.1万人,一度攻克了14座县城,并摧毁了西北敌方的补给中心——宝鸡。然而,在撤退过程中,我方遭受了严重损失。在这场战役中,警3旅受到了“临阵退缩”和“不服从命令”的非议,在军事史上留下了争议。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战斗一触即发,警3旅率先发难,直指监军镇,继而参与杏林、扶风的防御战,随后转战至屯子镇,执行解围任务,最终于良平地区设下防线,抵御青马,以确保西野主力得以顺利转移。在这系列激战中,杏林与扶风的防御战未能有效阻止敌裴昌会兵团的进犯,屯子镇的解围行动虽多次往返,却徒劳无功,使得野司陷入险境,这一事件遂成为11师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
1948年5月26日,在洛川土基镇,西野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对西府陇东战役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彭德怀将军主动承担了战役后期败北的主要责任,并对那些在战役中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指挥官进行了严厉指责。他指出:“4纵队的相关领导展现出极端的自由主义作风,这严重影响了队伍的内部团结,导致不良风气抬头,而正能量被压制,最终演变成不服从命令,多次错失有利战机,放弃或放走了本应消灭的敌人!”彭德怀愤怒地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就革命遭受的损失而言,简直应该处以极刑。
”他随后质问4纵队的领导:“既然你们有电台,完全有能力向上级请示汇报,即便敌军实力强大难以抵抗,也应当报告。可你们既未在岐山东侧抗击,也未在岐山西侧抗击。撤退时既不通知友邻部队,也不向我们通报,至少应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途中借宿于老乡家中,离开时都会告知房东,难道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就这么丧失了吗?”他最后强调:“战争是残酷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心,绝不能有丝毫疏忽。指挥员的失职必将导致意外损失和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会议对4纵队的警3旅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决定撤销旅长黄罗斌、警5团团长郭应春的职务。西野前委对4纵队及警3旅的批评和处分,让该部战士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

彭德怀司令员令部队西府进军。
鉴于对整体利益的考量,黄罗斌旅长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土基会议,自那以后数十载,他始终忍受着个人的委屈。1983年,某杂志上刊登的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将他刻画成《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因“不执行命令”和“擅离职守”而被撤职。黄旅长坚信这样的描述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遂于1984年12月20日致信原一野政治委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恳请组织进行核实。随后,总政治部、军委纪委、中央组织部共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长达三年的深入调查,于1987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黄罗斌同志历史上受处分问题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一历史疑案作出了明确的定论。
在西府战役期间,原总部的命令要求第4纵队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设防,以阻止并延缓敌军西进,从而为第1、2纵队攻占宝鸡提供掩护。然而,当胡宗南察觉我军意图夺取宝鸡后,迅速集结了11个旅的兵力支援宝鸡,对第4纵队警3旅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在此过程中,4纵副司令员阎揆一直亲自现场指挥警3旅。警3旅从扶风转移到岐山,再至纵队指挥部附近的麟游山脚下,每一步转移均严格按照纵队下达的命令执行。因此,黄罗斌不存在不执行命令的情况。
针对陇东战役中警3旅“不执行命令”的疑虑,经重新审查:该旅在参与屯子镇战斗后,遵照纵队指令,向三个不同方向推进。途中,4纵司令员王世泰接到前总指令,要求4纵前往屯子镇以东的南庄李家进行宿营,并负责警戒与掩护任务,该命令随即转达给了黄罗斌,黄罗斌随即带领部队转向南庄李家。当部队行进至距离南庄李家约十里的塬地时,听到了枪声,根据逃出的群众所述,黄罗斌误判敌人已占领该村,遂决定带领部队返回原路。在归途中遇到了王世泰,黄罗斌向他汇报了情况,并一同将部队带至三不同地区宿营。
彭总率领的前总抵达南庄李家后,未发现警戒掩护部队,遂立即调整了作战计划,由1纵临时派遣独1旅副政委颜金生率领一个团执行警戒掩护任务。独1旅在执行任务期间,以及后续途经南庄李家的6纵新4旅,均遭受了损失。黄罗斌在未派出侦察部队深入调查情况,也未向上级请示报告的情况下,仅凭听到的枪声和南庄李家逃出的群众反映,便将部队从南庄李家附近撤回,未能坚决执行前总下达的至南庄李家宿营并执行警戒掩护任务的命令,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终,我建议撤销对黄罗斌撤销旅长职务的处分,并提议相关部门依据本复查报告对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进行相应的修订。
本复查报告针对军史中关于“我军于占领宝鸡后,因立足未稳而匆忙撤退至陇东,导致前总陷入被动,此局面乃因北线阻击作战中的警3旅擅自撤退所致”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澄清。然而,在针对陇东战役中“违抗命令”一事的复查过程中,黄罗斌仍持有独到的见解。
“那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你们又怎会懂得?”
血战沈家岭
1949年8月,我军发起兰州战役,这场战役堪称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之最、战斗之最激烈的攻坚战。在这场激战中,11师承担主攻沈家岭阵地的重任,不仅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更为4军乃至一野的主力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家岭,地处兰州西南方约五公里处,是一座葫芦形状的山梁,面积广袤约百余亩。顺着山梁而下,即可直达华林山、满城,进而逼近兰州西关,对黄河铁桥实施控制,切断敌人退路,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堪比兰州的锁钥。青马部队在此建立了坚不可摧的环形防御体系,其中主阵地配备了由钢筋水泥构成的永久性核心工事,阵地前沿和两侧依地势险峻,筑有2至3层高耸的峭壁,并通过地堡群、战壕、铁丝网以及密集的地雷区构成了多层防线。驻守此地的敌军为青马的主力部队82军190师569团,该团战斗力强劲,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兰州周边的沈家岭,我11师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依照野战司的部署,第四军第十一师肩负起攻取沈家岭的重任。8月21日,该师三十二团对沈家岭实施了试探性的进攻。敌军顽强抵抗,凭借险要地形坚守阵地,我三十二团数度猛攻未果,损失惨重,最终被迫中止攻势。经过三天的休整与经验总结,第十一师决定调整战术,由三十一团正面发起主要攻击,三十二团则在夜间利用沈家岭西侧的沟壑进行隐蔽迂回,而三十三团则作为第二梯队支援。
8月25日破晓时分,各团趁着夜幕的掩护,悄然进入进攻的起始阵地。32团在夜色中行军超过七个小时,翻越了西沟,攀爬至沈家岭西侧的陡峭山坡,大约在五点二十分逼近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此刻,先头部队的五连不幸被敌军发现,敌军随即开火。由于地形对我方极为不利,32团不得不提前向敌人发起攻击,以期在站稳脚跟后迅速扩大战果。
面对我军的突然打击,敌军慌忙调动机动部队进行反击,同时害怕我军从正面发起进攻,便用炮火对我31团进行猛烈的压制射击。当时,师的指挥所与32团之间的电话尚未接通,情况观察不明确,我军的炮火无法及时支援。在敌军连续七次强有力的反击下,32团伤亡惨重,但指战员们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尽管如此,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他们无力进一步扩大战果,只得坚守已占领的阵地,与敌人在沈家岭侧后形成对峙。32团成功地牵制了敌人,为正面进攻提供了支援,直至战斗最终取得胜利。

11师攻克沈家岭前沿阵地。
5时55分,我军对兰州发起全面总攻。经过猛烈炮火的准备,31团采用爆破手段摧毁了险峻的绝壁,2营负责右侧,1营负责左侧,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首先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战壕,并占领了3号碉堡。至6时20分,在炮火的掩护下,部队又迅速攻占了敌军的1、2号碉堡。6时40分,部队突破了敌军的第二道战壕,成功占领了4、15号碉堡。
此时,敌军除派出一部分兵力监视32团方向外,其余主力转向正面,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双方展开了反复的争夺与激战。由于地形限制,我军炮兵难以充分发挥火力,步兵进攻受到阻碍,伤亡逐渐增加,31团随即投入3营参战,成功击退了敌军。敌军见形势危急,立即连续增调预备队,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对我军正面主攻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7时30分,11师命令33团从右翼加入战斗。两个团紧密协作,接连攻占了敌军的5、6、7、11、12、13号碉堡以及主阵地的17号碉堡。敌军见主阵地即将失守,急忙调动100师骑兵团、568团1营、保安4团、357师2团及129军工兵营等部队先后增援沈家岭。
敌军官一面狂呼“与阵地共存亡”,一面命令督战队驱使士兵冲锋,对后退者当场处决,组织整连、整营以密集队形,赤身裸体,手持大刀,狂吼乱叫,如狼似虎,蜂拥而来,在主阵地上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与拼杀。面对疯狂的敌军,我军指战员们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以压倒性的英雄气概,对敌军造成了大量杀伤。此时,我军伤亡同样惨重,部队建制混乱,弹药耗尽,一时难以补充,战斗受到了严重影响。然而,指战员们主动合并建制,从敌军尸体上搜集弹药和武器,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坚守已占领的阵地,击退了敌军的多次反扑。
随着战斗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指挥官在11时30分果断地将预备队的10师30团3营投入到沈家岭战场。31、33团依旧顽强地守卫着正面约300米的扇形阵地。30团3营抵达后,与坚守部队紧密协作,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攻。至13时,30团的1、2营也陆续加入战斗,我们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伤亡惨重,但我军愈战愈勇,对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经过从下午到傍晚的激战,敌方的士气和战斗力已然衰竭,出现了动摇的苗头。11师趁此有利时机,集结阵地上所有人员和武器装备,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连续挫败了敌人的7次大规模反扑。遭到我们致命打击的敌人狼狈溃逃,11师在10师30团的紧密配合下,乘胜追击,将大部分守敌歼灭。至19时,我军全面占领了沈家岭,兰州的锁钥终于被攻破。与此同时,敌方的营盘岭、马家山等主要阵地也被我军相继攻克,敌方全线陷入崩溃。友邻的3军控制了黄河铁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军各路大军随后相继涌入兰州城内。
26日凌晨一时,第十一师遵命在沈家岭北坡集结。鉴于伤亡惨重——战斗人员不足千人,其中第三十一团仅剩120人,第三十二团数十人,第三十三团300余人——部队随即转为第四军的预备队,并随军向华林山、满城方向发起攻击,同时击溃了部分残余匪徒。至中午十二时,兰州城内的敌军已被彻底肃清,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11师攻克沈家岭高地。
“攻克兰州的锁钥,4军再创辉煌”,一野和2兵团亦分别授予31团“勇猛顽强英雄团”和“真正顽强英雄团”的荣誉称号。
丰碑矗立“新西兰”
1952年6月,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其中第十一师直接隶属于西北军区指挥。在此过程中,第四军炮兵训练团以及第十师下辖的第三十团与第二十九团的三个营并入第十一师,同时第三十三团亦被裁撤。次年4月,根据上级命令,第十一师对所属的第三十团、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及炮兵团进行了番号的调整,分别更名为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以及炮兵第三零五团。从1956年至1958年,第十一师两次赴甘南地区平息叛乱,成功歼灭匪徒超过两万两千名,有效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确保了甘南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得以顺畅推进。
1959年三月,第11师接到紧急指令,奔赴西藏参与平息叛乱行动,期间共歼灭叛匪一万七千余人。次年十月,该师归入西藏军区领导体系,更名为陆军第11师,并肩负起日喀则军分区的职责。1961年,31团承接了中尼两国边界线的警卫任务,而33团则参与了中尼公路的勘察与建设。1962年十一月,11师投身于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战,击溃敌军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对被称为“二战王牌部队”的印军第4师给予了致命打击,彰显了国威与军威。33团表现出色,荣获集体三等功。
1963年以后,该师肩负起反击叛匪、强化边防建设与斗争等多项任务。1964年十月,其职责中不再包括日喀则军分区。1965年,为了牵制印军并支持巴基斯坦人民抵抗印军的入侵,11师遵照总部命令,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战略佯动。1967年,31团在周恩来总理、军委和总参的直接指挥下,在亚东中锡边境地区勇敢地反击了印军的武装入侵,捍卫了祖国的领土。此后,该师还承担了国防施工、营建、军训、生产等多项任务。

1979年四月,第十一师踏上入藏出疆的征程,沿途,藏族同胞热情洋溢,纷纷夹道欢送。
1979年4月,11师接到指令,被派往新疆执行任务,在乌鲁木齐军区的指挥下,肩负起建设与保卫新疆的重任。到了1985年,百万大裁军行动中,11师作为原一野的主力部队得以保留,并整编为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此时,原高炮73师的662团以及军区独立坦克团并入该师,使11师进入其发展历程中的巅峰时期。1987年,11师荣获新疆军区和兰州军区的表彰,被评为先进师党委。在解放军报庆祝建军60周年的特刊中,以“丰碑矗立新西兰”为题,对该师辉煌的业绩进行了长篇报道。
11师,这支被誉为“陕北雄师”的英勇部队,自1932年成立以来,历经磨难,勇往直前。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踏遍了陕、甘、宁、晋、蒙、青、川、藏、疆等九个省份,行程数千里。他们东临同蒲铁路,西抵喀喇昆仑,南至中印边界,北至毛乌素沙漠,这片近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留下了他们南征北战的足迹。他们参与了2660余次大小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走过了充满艰辛与曲折的成长之路。他们谱写了一曲逐鹿西北、捍卫西南的战斗史诗,展现了雄风激昂、气势磅礴的战斗风貌,铸就了“走遍新西兰,听从党召唤”的师魂。
在这支英雄队伍中,涌现出了许多英模单位和个人,如“能攻能守英雄团”、“勇猛顽强英雄团”、“罗局镇战斗英雄营”、“十颗红星炮班”,以及“全国战斗英雄”马宜生、田占德,“特等战斗英雄”王立功,“人民英雄”王学礼,“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董卫疆等。他们为部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外,这支队伍还培养出了2名大将、7名上将、17名中将和36名少将,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